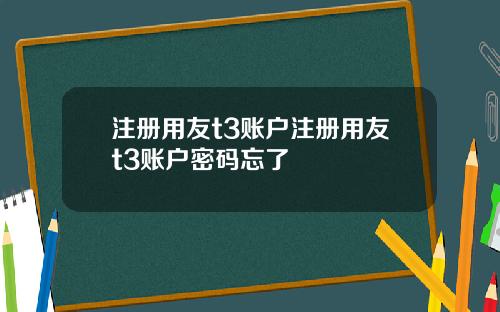“
了解一座城市,除了它的水光山色,街衢巷陌,便是它的历史人文了。其久远而深沉的律动,更能体现出物华天宝的本真。历史上,沙圪堵是个水草丰美的地方,鄂尔多斯草原伸展到这里时,地理、文化、经济的碰撞不可避免地发生了。就是在这方水土上,蒙古族兄弟修建了内蒙古草原上的第二座城镇,百年沧桑,这座发育得挺拔而神秀的小镇,诞生了一个又一个传奇。沙圪堵真是一处得人文雕琢的极具特色的小镇,漫瀚文化的浸润与繁衍,使它成为一个样板和窗口,成为一种展示;成为一道独具魅力、不可不读的景观。
是不是该有一个回顾或总结,抑或前瞻,为未来我们的发展提供一种启示,找出更宏阔的路径。
”
川上沙漏
沙圪堵的诞生,缘于一次又一次的文化冲撞,这片土地,在经历过无数次多元文化的渗透与沉积后,在无数次自然、历史的交锋与选择中成型了。这座城镇从它诞生那天起,融合就是它与生俱来的品性,因融合而生动,因融合而丰富,因融合而美丽,因融合而繁荣,因融合而超越,因融合而和谐。融合已成为它矢志不渝的品性。
公元1928年4月的一个黄昏,那森达赖回望了一眼身后层层叠叠的屋檐,义无反顾地辞别了他苦心经营了14年的那公镇(即沙圪堵镇,民国年间称谓)。在他身后,绚烂的大火照亮了整座城镇,火焰投射到纳林河水上,也投射到一座“品”字形的大院上,火焰的光亮在这座庞大的堪称蒙、晋、陕边地第一府院的青砖上,一阵亮似一阵的火光,烘烤着他的意志。那森达赖,也就是当时这座镇子的主人,连夜撤走了所有的商号,转移财产,实行坚壁清野。他决心只给入侵者留下一腔遗恨和一地瓦砾。他冷笑着,毁灭占据了他的每一寸神经,也成了他心中隐隐的快感。
沙圪堵镇,在行将毁灭的时刻,被一束历史的追光照亮,这座镇子,每一个巧夺天工的细节都清晰毕现,而那森达赖的面孔,则隐在历史的幽暗中,没有人看见那张缔造了这座镇子的面孔是什么表情。
那森达赖用一场大火修饰了他的强硬与不屈,并不是所有的蒙古族人都同意那森达赖的决断,也并不是所有的汉族人也都能接受这样的行为。他的行为是空前绝后的。侵略者愈是失望,便愈是变本加厉。沙圪堵被翻了个底朝天,欲望落空的侵略者,发怒穿冠,把一腔仇怨都泼洒到一切建筑物上,火上浇油,火光映红了天空,侵略者在狂啸的狞笑中将沙圪堵彻底化为了灰烬。沙圪堵,像一朵盛开的昙花,只留下了一个传说中的造型。现在,这朵超级昙花在人们的传说中变得越来越繁茂,那场大火,也成为准格尔历史上一场毒燎虐焰,从此一直迷离飘忽在历史的视野中。但它的背景,永远是一片焦土。
如果给史料一个归纳的话,可以这样表述:是沙圪堵,把准格尔蒙古族人呼啸的速度减化为风;是沙圪堵,把汉族人勤俭的品性固化为俗,融合形成了,漫瀚文化的又一个高峰出现了;是这把火,将一棵生长的穿天杨横空折断了……
一切缔造的奇迹,似乎均以毁灭来证实它存在的价值。也许,这座城镇的侵略者曾经相信,一把火会将这样的奇迹消灭。但谁也没想到,这座城镇活得更长久了。这场悲壮的大火,不仅没有结束它的生命,反而是它又一个新的开始。灾难,无形中推进了更深层次的融合。
无论它的缔造者和毁灭者多么强大,这座城镇,最终成为凌驾于所有强权与强人之上的存在,任何人都无法超越这个法则。在以后的岁月里,沙圪堵经历了共和国的哺育与呵护,愈发得成熟,愈发得挺拔。
每一座城镇,有人或许可以暂时篡改它的意志,但无法改变它的法则。历史赋予它的秉性,在过往的岁月中,有颠簸,也有飞跃,但它始终向着自然的方向生长。如果一座城镇,在经历了灭顶之灾后没有消失,那它就再也不会那么轻易地消失了。劫难,都无一例外地使它坚强,生长释放的能量,都无一例外地催化成花朵,在每一块砖石上灿烂地绽放。街巷、地名、风俗、文化,甚至传说,在岁月中延袭下来,那些不确定的事情混杂其间,发酵、萌动、演化,发出各种暗示。它们像绿叶素一样,滋养着这座城镇,使它变得深沉、丰厚、繁复。沙圪堵已不仅仅是一座城镇,它代表着某种文化,或者说,它是一种路径,提示着一种方向和可能。惟有时光筚路蓝缕,只有历史心领神会。
旧时蒙古族贵族妇女
一场商业奇迹无论多么轰轰烈烈,都不应该是一座城镇的终极目标。否则,它的发生与存在都将受到质疑。缺少强劲精神力量的渗透与灌注的城镇,就像一个没有灵魂的大力士,一阵风都可能改变它的形状,甚至将它击倒。一百年的时光,有时是会阻挡住一些锐气,但却阻挡不了它的生长。一百年,如果没有使一座城镇暮气沉沉,那么,它注定要崛起。它在大地上留下的一切,无论是鸿篇巨制,还是小家碧玉,都与历史的强度相关,与时代的高度相关,与文化的深度相关,与心灵的广度相关。它的遗传基因一次次被改写,岁月可能会消减去它的意志,却无法泯灭它的精神,这座城镇隐含的力量,不知将会获得怎样的释放。
天籁传声
那森达赖踌躇满志地唱着漫瀚调坐在沙圪堵的一座门楼上时,他怎么也没想到,他在选择历史的时候,历史也在选择他。此刻,漫瀚调的旋律和一百年前没什么两样,而漫瀚调的声音却没有一百年前清越,既潦草又俗陋。一百年前的漫瀚调,就像它的名字一样,被穿过云层的阳光擦亮,像一把锃亮的铜号,清新、婉转、悠扬。上世纪二十年代是沙圪堵的黄金时代,有人将它保存在史籍里,每一个细节都闪烁着迷离的光泽,也散发着霉味。民国初年,沙圪堵气势非凡,纳林河宽阔的河道旁,芦苇挺立,岸柳成行,树影婆娑。每当燕子在水面略过,或清风从叶间梳过,这座小镇的影子就会倒映在水面上。抬头望去,牌楼突兀地高耸,在万里晴空的映衬下现出清晰的轮廓。飞檐如翼,秀插云霄,仿佛凌空展翅的燕子。行人骑着毛驴走过牌楼,进入街镇,农夫肩挑的蔬菜,青翠欲滴,不紧不慢的驼铃声,仿佛来自天外。纳林河清澈的河水,从梦里流出,总是耀动着星光月色。这样的时光,属于往事、属于文化、也属于历史。
沙圪堵,不是一座简单的小镇,它令人肃然起敬。就在隔河的杨家湾,在远古无人知道的某一时刻,一群人点燃了一堆篝火。许多年后,一个名叫德日进的法国人在这堆篝火的灰烬中,发现了一枚古人类化石,德日进的兴奋还没有消退,他的同乡桑志华就发现了“河套人”化石。这个举世闻名的发现如果稍稍晚那么一点点,那么,留在史籍里的将不是萨拉乌苏,而是沙圪堵,历史将把沙圪堵推向另一种文化极致。
上世纪三十年代一个风和日丽的日子,一把在黄土里埋伏已久的青铜短刀,在距离沙圪堵不远的一个叫刘家渠的地方出土了。这个破土而出的青铜利刃,就是后来闻名遐迩的鄂尔多斯青铜器,而它最初的命名,叫“沙圪堵刀”,这是一个走乡串户的小贩的神来之笔,它只是随口以收购地而命名,就是这个微不足道的命名,为日后的考古发掘保留了弥足珍贵的信息。这把日后被专家称为“径路刀”的匈奴兵器,在划出一道炫目的寒光后,成为了沙圪堵不多的几个传说中经久不息的传奇。
没有比郭伋竹马的故事更能体现这片土地的精神与气度了。郭伋与沙圪堵的孩童,共同完成了中国历史上最早记录、也最为著名的诚信故事。沙圪堵书写了一个民族、一个国家最可贵的品质之一。沙圪堵,它潜伏在历史的深处,以一种神奇的力量,推动着一种精神的传承与跨越。既在我们的视野之外,又在我们的精神之内。这是一片曾经每一块泥土、每一块瓦砾都凝结和浓缩着历史的土地,它静默在时光的深处,如果你愿意,你甚至可以听到历史在泥土中穿行的足音。匈奴人的马蹄在踏碎罗马帝国的美梦之前,剽悍的铁骑先在这里止步了。他们决定接受汉朝的建议与安置,在这里歇下狂野的马蹄,修建他们自己的宫城。草原帝国的都城,千里迢迢迁到了这里。一部神奇王朝的历史从此写在这片青青的草地之上。谁敢说,那把青铜的短刀,不是一个彪悍的匈奴王丢弃的武器。我们几乎可以从这把短刀上读出一个民族的沉浮来。你会不由自主地去想,匈奴人是从哪里来,又向哪里去?为什么会从历史的舞台上销声匿迹了?湳水,那条长满翠竹的匈奴兄弟饮马的清流,是消失在游牧长城的铁蹄下,还是掩埋在问鼎中原的尘埃里,抑或是干涸于环境恶化的溃退中?
沿着沙圪堵的一棵老柳树追寻,源头是一片茂密的榆林。一百年前,水草丰美的原野在夕阳下退去最后一抹霞光,像打开一部史诗,历史的细节风华绝代,农业文明的气质比想象更丰富,比历史更深沉。两汉时期,湳水边上有座著名的县城,富昌和美稷。富昌是西河郡的郡治。“匈奴王印”和“西河农令印”这两个闪光的器物,分别出土于这两座县城。它们的破土而出,像是一个路标,更像是一个破折号。这两个东西放在一起,辽阔无边,充满了包容性与亲和力。匈奴王印的容量,可以验证这个地区的广度;西河农令印则让我们看到历史的长度。这是岁月年深日久的两扇窗户,左边这扇可以看到蓝天上邈远的大雕的弧线,右边这扇可瞭望到大地上一望无际延伸的犁迹。一个庞大帝国的秘密,就蛰伏在这两枚铜印的阴文字体中。
牧野之间
曾经鲜花遍布歌声萦绕的原野上,生长着漫瀚调,现在,它的辽阔与孤独已经消失殆尽。很古老的时候,沙圪堵是海,大海从沙圪堵突然退下去时,迄今留下的是起伏的沙丘,就像它的名字一样。(我曾在沙圪堵的沙砾中,捡到几片鱼化石,祖母说;你拣到海了!这是祖母留给我最诗意的句子。)历史经过沙圪堵时,留下的是传说,一些古老的民族在这块土地上风一样地消失了,沙圪堵是保存多民族方言最多最丰富的地方,也像它的名字,是一块语言的化石。时光浸滤沙圪堵时,美丽的歌声回旋着、上升着,雕刻出沙圪堵的节奏与旋律,就像漫瀚调的别名是沙丘调一样,坦荡,热烈,色彩斑斓。很多人说,他们一辈子也不想离开沙圪堵,因为沙圪堵既让他们安逸,也让他们沸腾。没有深刻体验的人,说不出这样的话,也读不懂这样的话。曾经滔滔不绝的湳水,最终在深红色的陶罐上留下了流畅的波纹,也给历史赋予了非凡的想象力。湳水,这条美丽而丰沛的河流,总是充满神灵的奇异,弥漫着氤氲之气,仿佛上天的神来之笔。造物弄人,沙圪堵本来是个充满水汽的地方。湳水,总是让人憧憬遥远,林胡、楼烦、匈奴、乌桓、鲜卑、突厥,这些永恒的名字,虽然在历史上匆匆出现,又匆匆离去,但却在这片土地上留下了无数的灿烂,文明的碎片,像漫天的星斗。即使这些灿烂可能残缺不全,甚至布满裂纹,正是这些裂纹,一次次使历史变得清晰、明媚、完美。
沙圪堵,就像博物馆里一只保存了五千年的彩绘陶罐,时间永远无法将它风化。这是沙圪堵最优美的造型,从泥土中来,到灵魂里去。
怀念,是人类最不可或缺的精神柔情,它是一种灵魂的温度。沙圪堵,是祖母塞进我身体里的一支温度计。
旧时参加婚礼的牧民
你不能想象,沙圪堵人,盘腿席地而坐,放眼四野,漫瀚调像心中的泉水,似乎一张口,就流淌成一条河。风中围坐的眉目慈祥的父老乡亲,就成了大地的中心。他们就是这片大地的主人,一切仿佛触手可及,世界可以安坐拥有。沙圪堵,像传说中的一片白云,静止在蓝天上。承受它,需要一个支撑点——漫瀚调就是这个支撑点。找到这个支撑点,也就找到了这片土地的精神原点,即使你远游到天边,只要一听到漫瀚调亲切的旋律,故乡就在你身边。只要你一开口,你也就将故乡带到了天边。只要听到漫瀚调,你就能够确定自己的位置,与青草飞鸟同在,与默默降生的小生命同在,像是听到了自己的心跳,你就是漫瀚调中大地的心脏。
漫瀚调,准格尔人生命的胎记,一首历史的抒情诗!
天日昭昭
一百年,沙圪堵亲切而具体,与湳水默默相对,与天籁静静相守。这是留在旧时光里的沙圪堵。沙圪堵这个名字,丝毫不张扬,普通的就像空气,它似乎只是传达着这个城镇最初的形态。但这形态,不很长,二百年不到,但很纠结,有痛感,令人深思。很多人不满足这个朴素的名字,可能是嫌它“土气”,一定要读出一些深奥来,一会儿说它是蒙语,一会说它是满语。这些都是画蛇添足,是亵渎,也是徒劳。沙圪堵,其实只是一个蒙古族人沙格都尔的牧地,久了,就被走西口的汉民取谐音叫成了沙圪堵。留着吧,这是个历史时空、地理迁变的标本。沙圪堵,也还朗朗上口,也还朴朴素素、自自然然,它属于天、属于地,也将属于永恒和风。
漫瀚调,就是天籁,用灵魂倾听,用生命传唱。一代又一代地被遗传下来,成为一种天赋,绽放在生命的深处。它是沙圪堵的灵魂,也是准格尔的旗帜。漫瀚调徜徉过的地方,留下的是芬芳;芬芳弥漫的地方,也是漫瀚调升腾的地方。漫瀚调袅娜着、迤逦着,天地赋形,芬芳遂人,鲜花般围裹着你,启迪着你,陶醉是一种生活的方式。漫瀚调是一蓬盛放的鲜花,沙圪堵便是袭人的花蕊。
方言占据了沙圪堵,凡是穿过方言的物质与精神,都烙上了沙圪堵的色彩、气味,甚至形态,形神互现,挥之不去。我们在它的浓荫下安睡,也在它的阳光里进出,时间长了,方言成了我们身体的一部分,生命的标志。
沙圪堵是一种人格化的刻度,世上多了一个想象的高度,人生就多了一种抒情的深度。这种独一无二的方式,将他们的悲欢唱到今天,唱到天边。漫瀚调是一种释怀,也是对生存的确认。如今,我们看到的沙圪堵,远比历史上的任何时刻都妖娆,失去简单、质朴、清洁的土地,就会失去漫瀚调。它新的气质与形象,正在一代又一代的塑造者手中形成。经过百年的沉积之后,这座城镇的接力棒被传到了一代又一代的建设者手中,在传递中,它的光泽与能量正一次次被改写,无论它还经历多少风雨,都将成为雕塑者勇气、智慧、胆识、意志、责任与担当的试金石。
沙圪堵,这片曾经长满竹林的土地,尘霾渐起。那些岁月中美好的传说,那些消失在历史深处的竹影,让人隐约看到了这片土地精神源头的神韵。仿佛留在风中的指纹,每一条旧街道,都像是漫瀚调休止的一个波折音;每一条新展开的道路,又像是一个又一个乡愁的起点,纠结在一起,回旋着、盘升着、演变着……从四面八方来到这里的外乡人,操着各自的方言,南腔北调,却十分融洽自然……
市井
任何一个地方的建城史,都是一部经济史,一部人文传记,一把历史的篦梳,也是一把雕刻刀,时光在握,一笔下去,天上人间。无论是那公镇还是沙圪堵,它的属性在它设立时就早已存在了,我们只是不断地去审视它、接近它、盘点它、翻新它,试图超越它。
时光更迭,改变的只是容颜,不变的却是精神,这便是包容、和谐、大同。时光在雕刻它,它也在雕刻时光。这是一种悠久的互补,群体的美声。这也是一种广泛的协调、深沉的融合、辽阔的共鸣。它呈现出一个个被刻画的形象,却没有刻画者具体的名字,这是它辽远的起点,也是它美丽的根源。一切文化的基层,都以地理环境、气候生态、自古风习为构筑。沙圪堵,是两千年来漫瀚文化一次大激荡、大汇聚、大梳理的一个交接点,是一个可以作为我们解读中华文明的支撑点、落脚点。
沙圪堵有界,漫瀚文化无疆。
沙圪堵,是一个容器,它的容量似乎可以盛得下我们所有的梦想与雄心。